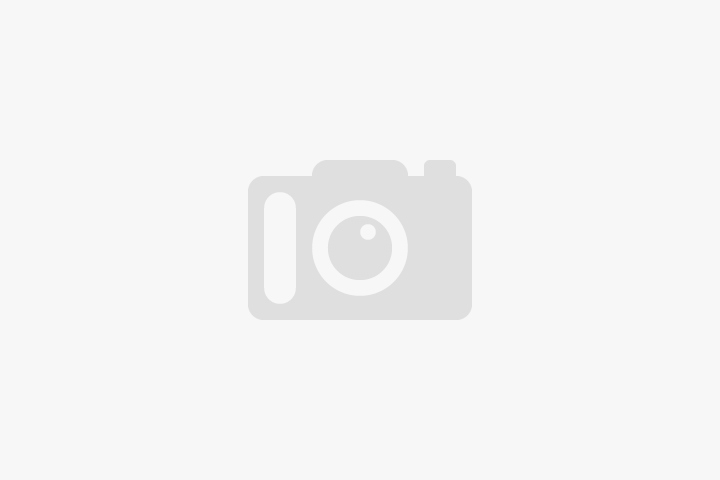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半个世纪后,我还在想念澡溪母校的几位恩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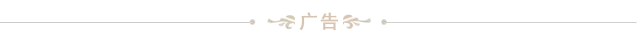

教师节期间,我在奉新信息网发表了三篇回忆恩师的文章后,意犹未兴,再向读者介绍几位半个世纪前澡溪中学的恩师。
说起我与澡溪中学的结缘挺有意思。上世纪60年代奉新的小学升初中,由全县统筹招生。甘坊中心小学属于山区片,山区片的小学毕业生参加升学考试后,成绩好的按惯例将分配在上富中学就读,成绩差的只能上半工半读的甘坊职业中学。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我和其它五位成绩好的学生却阴差阳错地被澡溪中学录取。当年我心里还有点憋屈。现在回忆起来才知道是老天赐福。因为澡溪中学有着悠久的的办校历史,抗日战争时期,奉新县县立中学就曾迁址澡溪;更因为它有着强大的师资力量,我新入校的那个学期,澡溪中学就有六个大学毕业的教师,这在全县山区公社一级的中学是绝无仅有。

我到澡溪中学认识的第一位老师是班主任谌志茂,极有意思的是,认识他的第一天,他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印记。
他在报名表上正要填写我的名字时,突然抬起头问:“你叫龙光河?”我说是呀。他笑着说这个名字不太好,龙是靠水生存的,河水都光了,龙怎么游得动啊?是不是可以把“光河”改成“江河”?我说在龙氏家族里,“光”是我的派号呀?他说现在姓氏里用不用派号已经不是那么讲究了。你看,如果改成“龙江河”,浩瀚的江河里,游弋着一条生气勃勃的龙,多有气势啊!我想想有道理,就点点头答应了,从此我的人生符号或者说是人生印记就正式更改了。
我没有研究过姓名风水学,但大半辈子的人生历程令我相信,姓名的确能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健康状况、发展方向、事业走向;而且我还有点相信,姓名犹如一个全息密码,从中可以读出许许多多的信息。
谌老师给我改名后,我真的得益不少,与陌生人第一次交往后,往往别人将我的相貌遗忘了却还记得我的名字;尤其是酷爱文学创作后,收到过我投稿的刊物编辑老师,大多第一眼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让我得以有更多向他们求教和交流的机会;不少读者也是因为记住了我的姓名才更多地去关注我的作品。年岁越长,越来越觉得我仿佛就是奔着这个名字而来到世间的。怎么说谌老师都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贵人里的其中一位。
谌老师不仅书教得好,篮球也打得特别棒。那时候澡溪中学的篮球队非常有名气,县里、东垦、兄弟中学的球队经常来与我们学校一决雌雄,每逢比赛,操场两边整整齐齐地坐满了当啦啦队的师生,当谌老师异常灵活地带球过人后紧接着一个漂亮的三步跨栏将球准确地投进篮球框时,学生们就会发疯似地狂欢起来……

开学不久,学校又调来了一位新老师,是广东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名叫罗淦先,他接替了谌老师的语文课。罗老师个头不高,面孔黧黑,如果在外面初次遇见,没准会以为他是当地老表。可是他一走上讲台,那不紧不慢的说话节奏,那抑扬顿挫的声调,那收放自如的神态,秒杀了教室里每一个学生。有一件事可以佐证当初我是多么地痴迷他的讲课: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每次在电视里看到百家讲坛里的易中天教授,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罗淦先老师,甚至产生一种错觉,镜头里的易中天就是罗老师,罗老师不仅长得像易中天,连讲课时的神韵都惊人地相似!
有一天下了课,他把我和另外一个作文写的好的同学叫到操场一角,问我俩长大了想从事什么职业,问得我和那个同学一脸茫然;接着又问我俩想当作家吗?他说如果想当,那么从现在起就开始每天记日记,而且不能间断。当时我虽然不敢响亮地回答想当作家,心里却撒下了一粒种子,萌生了一个朦朦胧胧的梦想,而且从那一天开始养成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现在我箱子里珍藏着的多本日记,为我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可以说,如果没有罗老师的点拨,也许我就与从事了一生的文化艺术工作无缘了。
还有一件事令我难以忘怀,十年后我在奉新县文化馆主编《百丈山》文艺小报时,搞了一次短篇小说征文,我惊喜的收到了已在奉新一中任教的罗老师一篇作品,开作品讨论会时,我非常拘谨,我怎么能对恩师的作品品头论足呢?会议休息时,罗老师把我叫到一边,鼓励我大胆点评,不要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就不敢指出作品中的不足,那一刻,我才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虚怀若谷”。
不久,罗老师调到省教育学院去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去年我多方打听他的情况,准备专程去看望他,没料想他因病去世已经好几年了,人生就是这样遗憾,这样无奈!

龙强老师来自全国著名的“将军大县”江西永新县革命老区,出生于革命烈士家庭。在澡溪中学工作时谈恋爱了,女方是澡溪公社农村信用社的小王。本来这是郎才女貌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大好事,不料“文革”开始,问题就来了:龙老师是烈士后代,又是学校的领导,而小王家庭成份不好,于是造反派头头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站稳阶级立场,与小王断绝恋爱关系。龙老师不从,为了给他施压,造反派对小王进行了残酷的批斗,龙老师依然不从,于是连他也遭受了批判,他还是不从,毅然抛弃大好政治前途,义无反顾地与小王结为夫妇。从此你恩我爱,风雨同舟;生儿育女,锅碗瓢盆;相濡以沫,执手至老。龙老师在奉新县第一中学退休后,傍晚时,沿河北路常常会出现他们夫妇俩的身影,当年的小王总是笑意荡漾地搀扶着龙老师的胳膊在散步,与披在他俩身上的晚霞,构成了一幅温馨无比的画面。
龙老师只教过我很短一段时间的政治和数学课,我从他身上学到更多的是人生道理,他的婚姻让我懂得,爱情可以讲门户相对,可以讲经济条件,但是也可以纯粹!

张发相:慈祥如父,敦厚如山
张发相老师(已故多年),他白白的皮肤,一张阿弥陀佛像似的大圆脸,在学校管总务。
当年我们从甘坊一行去澡溪上学的六人都是十二、三岁的男孩子,从来没有独立生活过,张老师怕这几个乳臭味干的毛孩子不能自理,我们在甘坊粮站打的拨粮证和买的一个月饭菜票全部由他代为保管。他专备了一个小本儿,分别写上我们的名字,下面登着我们买饭菜票的数目,每次只给我们每个人发五斤饭票和一元菜票,这样我们就不会弄丢了,如果没有他不厌其烦的呵护,我们几个很可能会把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我从甘坊去学校,步行到上富时,没赶上奉新到澡溪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家住上富的张老师刚好骑着自行车回学校,他路过车站时看见我愁眉苦脸,便叫我搭他的自行车,上富到澡溪基本上都是上坡路,但还是有一些平路和下坡路,毕竟节省了不少体力。为了安全,张老师叫我坐在自行车前面的三脚架上,每下完一个陡坡便利用惯性去冲刺一个上坡,一直到脚踏板实在踩不动时,他才停下来,为了防止我停车时摔倒,还用双臂牢牢地护住我,那一刻,我闻到了父亲身上的气息。
当年我很调皮,常常做一些出格的事。有一天我的身上的长裤被一口钉子划破了,大腿也露了出来,没有裤子换,我就穿了一条短裤罩住长裤,张老师见我如此不雅,把我叫进他的房间,令我脱下裤子,找出针线帮我缝补起来。当年我看到他补裤子时不时地用手去扶鼻梁上快要滑落下来的老花眼镜,觉得挺滑稽,忍不住想笑,现在回想起来却鼻子有点发酸。
更有一次,我随公社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回来已是深夜,因为第二天还要继续下乡,我不愿意解开随身所带的被子,便到张老师房间蹭睡,我脚下一双橡胶套鞋穿了十来天,我怕臭气熏着张老师,特意用热水泡了脚才上床,第二天又乐颠颠地随队下乡了。几个月后,张老师在县城开会时遇见我了父亲,他笑呵呵地说:“你哩江河跟我睏一夜,恰咯斋,被窝里臭咯半个月!”我听说后也暗自发笑:张老师咋那么能忍,当时怎么没听到他吭半声呢?

殷德先老师毕业于江西共大。他分到澡溪中学时,足够吸引全校师生的眼球,他是北方大汉,身材魁梧,浓眉大眼,一米八的个头,头戴一顶硬边帽檐还有两只护耳的蓝布棉帽。他的篮球打得比谌志茂老师还棒。每隔十天半月,县里就要借调他去组队参赛。记得他好像是教我们的化学课,我们更多的时间是缠着他教我们打篮球。可能是刚出校门不久,他给我们上课时有点拘谨,教我们打篮球却是如鱼得水,十分自如;他还经常一个人与五六个学生对阵,最终学生们还是输在他的手里,令我们对他崇拜有加。北方人性情耿直,热情奔放,我们这些学生更愿意与他搅和在一起。一到傍晚他那间紧靠天井的小房间里,总是挤满了嘻嘻哈哈的男女同学,气氛十分融洽。他调来以后,我打篮球的水平日益长进,身体素质也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可敬可爱的殷老师为我们单调的校园生活添色不少。
令我喜不自禁的是,我进县文工团不久,县里为了篮球运动的发展,将他也调到了县一中。从此,只要有他参加的篮球比赛,我就会早早来到县工会的灯光球场,怀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一睹他的风采。
去年,上海知青在九仙举办了一次的大型纪念活动,他与夫人也远道赶来出席,他见到我,慈祥得令我心颤;看到精神矍铄的他与夫人蔡可慧姐姐,我真是打心底里高兴!

限于篇幅,对母校的老师不能逐一介绍,但我还是想各用一句话概括给我留下过深刻印象的其他几位:不言自威的吴润芳校长(已故);厚道朴实的温必其校长;满肚子故事爱生如子的刘弦功主任;温文尔雅的甘树含老师;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的卓天成老师(请见文中“澡溪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合影”三排左一,已故);学生心目中的乒乓之神彭正禄老师;待人谦和的黄爱群老师(二排右三);幽默风趣的蔡名涛老师(已故);会跳芭蕾的罗会柯老师;会拉二胡的吴金莲老师(二排左四);会作曲的邹德树老师;多才多艺的魏远荣老师(澡溪中学有两个魏远荣老师);英年早逝的熊英儒老师(二排右四)……
想起母校的每个恩师,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画面,我好想大喊一声: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是想你们!
-

华林广场四小周边
冯川镇110㎡| 3室2厅 0元 面议 -

四季花域
冯川镇120㎡| 3室2厅 1500元 面议 -
城南新吴路小区
冯川镇80㎡| 3室2厅 500元 面议 -

狮山西大道农牧渔场宿舍
冯川镇100㎡| 3室2厅 600元 面议 -

洗沙路东门
冯川镇160㎡| 3室2厅 800元 面议 -
奉新一中宿舍区
冯川镇40㎡| 1室1厅 580元 面议 -
冯田开发区
冯川镇60㎡| 2室1厅 200元 面议 -
伟星三期北面
冯川镇40㎡| 1室1厅 600元 面议 -
锦绣江南
冯川镇90㎡| 2室2厅 1500元 面议 -
华林广场后
冯川镇30㎡| 1室1厅 580元 面议 -
伟星滨江花城15栋一单元201
冯川镇128㎡| 3室2厅 1500元 面议 -
中贤水岸丽都
冯川镇100㎡| 2室1厅 1200元 面议
-

小产权王家
冯川镇133㎡| 3室2厅 32万 面议 -

狮山公寓
冯川镇118㎡| 3室2厅 66万 面议 -

冯城嘉苑
冯川镇133㎡| 3室2厅 59万 面议 -

滨河壹号
冯川镇127㎡| 3室2厅 66万 面议 -

小产权六小附近
冯川镇140㎡| 3室2厅 32万 面议 -

江南首府
冯川镇116㎡| 3室2厅 59万 面议 -

龙山大道附近
冯川镇120㎡| 4室2厅 69.8万 面议 -
塞纳广场
冯川镇49㎡| 2室1厅 38万 面议 -
新安花园
冯川镇120㎡| 3室2厅 15万 面议 -

雅阁春天
冯川镇56.4㎡| 1室1厅 18万 面议 -

金穗广场
冯川镇96.91㎡| 3室2厅 58万 面议 -

金鹏•公馆壹号
冯川镇124㎡| 3室2厅 73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