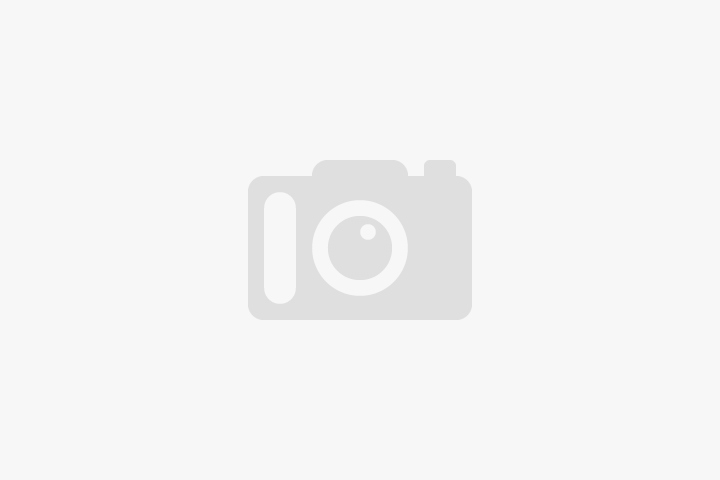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老罗坊故事】再说上街头的“进士第”,这里藏着百年风雨岁月苍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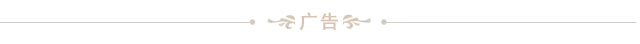


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二:
“进士第”难民曾在这里躲避

甘道友
罗坊历史上的古建“进士第”与“司马第”并排建于潦河岸边。从建造风格和式样以及第宅内部结构来看,两幢古建几乎相近,但“进士第”的建造时间要比“司马第”更晚些,约嘉庆年间,岂今二百年左右。


“进士第”系三幢进,天井也是成“品”字形,建筑面积与“司马第”多了一排边房,后墙的高度却比“司马第”低一些。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两米,巷深三十米,薄条石铺面,光滑平整;夏天微风轻拂,在巷里乘凉特别舒爽。

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2米,宽深30米
已90高龄的大姐甘道菊告诉我,解放前我父母从港下村搬到罗坊街上的时候,先居住在“进士第”的边房,后来才到“司马第”对面住。“进士第”这一排边房也曾出租,主要为来罗坊做生意的一些商贩提供住宿方便。大姐说:战乱时,“进士第”是难民的聚散地。不知从那里来的难民蜂拥而至,难民拖儿带女,烂手烂脚,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整个“进士第”都挤满了难民,生活境况凄苦,生存环境恶劣,隔三差四就有一个难民离世。难民死后没有棺木安葬,多般是一床草席包裹,由当地的“八仙”抬到田背的“脑子山”掩埋……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投放细菌,我大姐左手的食指至今还有一个疱块,麻木疼痛,几十年无法消失,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国耻家恨,岂能忘记。

大姐左手的食指至今麻木疼痛……
民国期间,“进士第”因人群来往居住复杂,闲时无所事事的人一度赌博成风。一天,来了几个货客,他们系好船只上岸,在街上一家酒店吃过晚饭后来到“进士第”边房借宿,晚上便和房东们聚在一起推起了“牌九”。不料赌到月落星沉,鸡鸣司晨,这几个货客还沉溺于赌桌,久久不肯收场。当晨曦初露,他们几人擦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来到岸边一看,货船不见了……几个货客望着被晨雾笼罩悠悠流淌的潦水,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有老人说过,这条货船是被华林山上的盗匪劫走,船上的货物价值不菲。事件的发生说明当年的治安不严,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沉重的教训告诉人们沉迷赌博总不是好事,不是损财,便是伤身。

边房依旧存在,只是人去房空……
查阅樊明芳老师编著的《罗市文史钩沉》第50页记载:从淳祐十年(1250)至同治七年(1868)进城乡(罗坊)先后考中进士9名,其中有7名是严氏族人,嘉庆年间考中的有严晖吉(嘉庆六年,任职湖南道洲知州)、严拱(嘉庆六年,直隶天津府知府)两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进士第”约建于嘉庆年间,而严晖吉和严拱在嘉庆六年考中进士。那么,建造“进士第”的人就可能在他们两人之间。

古代科举制度考试进级阶位由低至高为: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就进士而言其学历相当现在的博士或教授,其职位而言相当于现在的厅级领导。由此看来,古今的人如出一辙,要想建造一幢大院,要么有官位权势,要么有银子钞票。
“进士第”从外观看没有富丽堂皇的气派,俨然是一幢大的民宅,就宅内的布局结构来看也极为普通,但房间的设计错落有致,空间的利用恰在好处,采光极好,几乎没有“暗室”。由此可见,“进士第”的建造者当年建宅时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所以,“进士第”给人的感觉是紧凑而不失宽敞,简朴而不失典雅。

老罗坊的“进士第”居住的人群都是杂姓,前后进出也较为频繁。到解放后相对稳定居住的家庭有农民刘于志,罗来旺、刘崇元、陈家洗、朱向东,居民陈玉书、陶方盛、张洪志、小老陈、周诚明、阙英榜、严奇美、廖婆婆、克茂公等。到八十年代,老一辈的人基本离开人世,后生代的住户也陆续搬出。

去年冬,有几个“小毛特”进入“进士第”盗挖财宝。“小毛特”以为历史上富庶人家埋下了金银财宝,殊不知这里解放前动荡不安,解放后居住的人群也近乎贫民居多,那有金银财宝下窑,结果“小毛特”两手空空,白费一番心血。如今的“进士第”和“司马第”一样无人居住,已成为政府不允许拆除,但修缮又没有钱的尴尬局面。“进士第”的后院已塌,满目疮痍,杂草丛生,一屋凄凉……

(下篇预告: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三:“包家”三幢进族人考武举。)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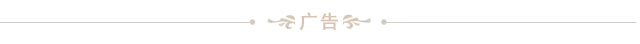


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二:
“进士第”难民曾在这里躲避

甘道友
罗坊历史上的古建“进士第”与“司马第”并排建于潦河岸边。从建造风格和式样以及第宅内部结构来看,两幢古建几乎相近,但“进士第”的建造时间要比“司马第”更晚些,约嘉庆年间,岂今二百年左右。


“进士第”系三幢进,天井也是成“品”字形,建筑面积与“司马第”多了一排边房,后墙的高度却比“司马第”低一些。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两米,巷深三十米,薄条石铺面,光滑平整;夏天微风轻拂,在巷里乘凉特别舒爽。

两古建共一个巷口,巷宽2米,宽深30米
已90高龄的大姐甘道菊告诉我,解放前我父母从港下村搬到罗坊街上的时候,先居住在“进士第”的边房,后来才到“司马第”对面住。“进士第”这一排边房也曾出租,主要为来罗坊做生意的一些商贩提供住宿方便。大姐说:战乱时,“进士第”是难民的聚散地。不知从那里来的难民蜂拥而至,难民拖儿带女,烂手烂脚,个个衣衫褴褛,骨瘦如柴……整个“进士第”都挤满了难民,生活境况凄苦,生存环境恶劣,隔三差四就有一个难民离世。难民死后没有棺木安葬,多般是一床草席包裹,由当地的“八仙”抬到田背的“脑子山”掩埋……日本鬼子侵略中国投放细菌,我大姐左手的食指至今还有一个疱块,麻木疼痛,几十年无法消失,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日寇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国耻家恨,岂能忘记。

民国期间,“进士第”因人群来往居住复杂,闲时无所事事的人一度赌博成风。一天,来了几个货客,他们系好船只上岸,在街上一家酒店吃过晚饭后来到“进士第”边房借宿,晚上便和房东们聚在一起推起了“牌九”。不料赌到月落星沉,鸡鸣司晨,这几个货客还沉溺于赌桌,久久不肯收场。当晨曦初露,他们几人擦着充满血丝的眼睛,来到岸边一看,货船不见了……几个货客望着被晨雾笼罩悠悠流淌的潦水,面面相觑,哭笑不得。有老人说过,这条货船是被华林山上的盗匪劫走,船上的货物价值不菲。事件的发生说明当年的治安不严,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沉重的教训告诉人们沉迷赌博总不是好事,不是损财,便是伤身。

查阅樊明芳老师编著的《罗市文史钩沉》第50页记载:从淳祐十年(1250)至同治七年(1868)进城乡(罗坊)先后考中进士9名,其中有7名是严氏族人,嘉庆年间考中的有严晖吉(嘉庆六年,任职湖南道洲知州)、严拱(嘉庆六年,直隶天津府知府)两人。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进士第”约建于嘉庆年间,而严晖吉和严拱在嘉庆六年考中进士。那么,建造“进士第”的人就可能在他们两人之间。

古代科举制度考试进级阶位由低至高为: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就进士而言其学历相当现在的博士或教授,其职位而言相当于现在的厅级领导。由此看来,古今的人如出一辙,要想建造一幢大院,要么有官位权势,要么有银子钞票。
“进士第”从外观看没有富丽堂皇的气派,俨然是一幢大的民宅,就宅内的布局结构来看也极为普通,但房间的设计错落有致,空间的利用恰在好处,采光极好,几乎没有“暗室”。由此可见,“进士第”的建造者当年建宅时首先考虑的是实用。所以,“进士第”给人的感觉是紧凑而不失宽敞,简朴而不失典雅。

老罗坊的“进士第”居住的人群都是杂姓,前后进出也较为频繁。到解放后相对稳定居住的家庭有农民刘于志,罗来旺、刘崇元、陈家洗、朱向东,居民陈玉书、陶方盛、张洪志、小老陈、周诚明、阙英榜、严奇美、廖婆婆、克茂公等。到八十年代,老一辈的人基本离开人世,后生代的住户也陆续搬出。

去年冬,有几个“小毛特”进入“进士第”盗挖财宝。“小毛特”以为历史上富庶人家埋下了金银财宝,殊不知这里解放前动荡不安,解放后居住的人群也近乎贫民居多,那有金银财宝下窑,结果“小毛特”两手空空,白费一番心血。如今的“进士第”和“司马第”一样无人居住,已成为政府不允许拆除,但修缮又没有钱的尴尬局面。“进士第”的后院已塌,满目疮痍,杂草丛生,一屋凄凉……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自定义html广告位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