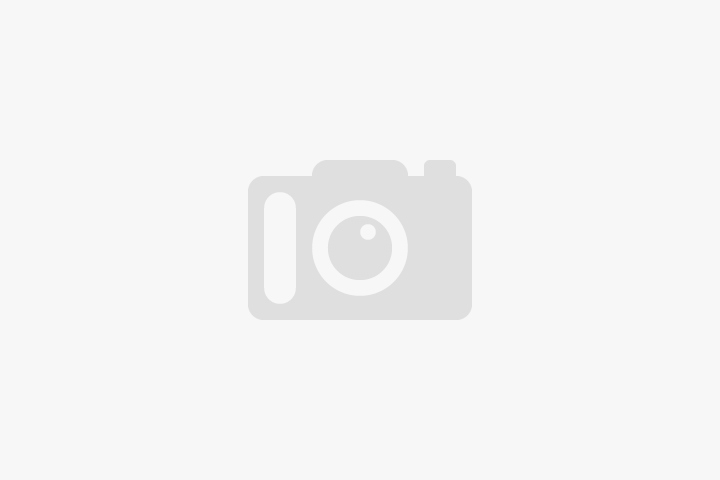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老罗坊故事】罗市有一处“鸳鸯地”,揭秘它曾被世俗误解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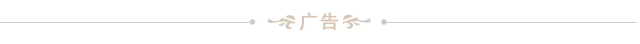
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九:“鸳鸯第”其实是“鸳鸯地”
说起老罗坊古建“鸳鸯第”(地),恐怕只有九十岁以上的老罗坊人见过它的存在,后辈只是听说过老罗坊上街头有一处古建“鸳鸯第”(地)而已。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字的释义:第,表示次序:例如第一。表示科第:古代科举中称考中的叫及第,没有考中的叫落第。第,还表示贵族公卿的住宅。而所谓的门第,就是从这里衍生而来,通常指家世名望显赫。而“地”的字义非常广泛,如地方、地址、地点、地域、地貌等等。“鸳鸯地”也就是地点所指了。
尽管“鸳鸯”是爱情忠贞的像征,但如果老罗坊的一家名门望族建住宅用“鸳鸯”二字作为门第之称,不仅不符合身份的彰显,也会让人有误“风月”场所之嫌。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罗坊历史上这里就叫“鸳鸯地”,而不是权势贵族的住宅“鸳鸯第”。民间把“鸳鸯地”叫成“鸳鸯第”是字音上的错误。

“鸳鸯地”保存完好的边房 
边房入口的石巷门
老罗坊古建“鸳鸯地”紧挨着“文林第”而建。笔者在写这篇文章前,先后走访了老罗坊几位高龄老人,又在查阅罗坊“严、罗”两大家族族谱的基础上,也对“鸳鸯地”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察。由于笔者手上可查阅的资料有限,尽管没有找到“鸳鸯地”古建有价值的信息,但也搜集到了关于“鸳鸯地”的一些传说和趣事。
老罗坊虽然开埠时间早,但进入鼎盛时期,还是从明朝商人罗英叔建镇开始。明朝建镇后的罗坊成为除奉新县城之外唯一的一个街道最完整、地域最繁荣、商贸最活跃、水陆最方便的城镇。“一河货船穿梭,三里商铺相连;日有千人游织,夜临万盏明灯”。这首民谣也许是对当时罗坊繁华似绵的真实写照。

见证了老罗坊繁华的潦河,如今已水位下降,河床见底
罗坊建镇后,因水陆两运非常通畅,来做生意的商贾和游人络绎不绝,这就给餐饮、住宿、娱乐等带来了极大的商机。民间传严氏家族中有一商人春节从外地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目睹罗坊新镇一派繁荣景致,头脑灵光的他当即看准了商机,便在大街繁华地段“上街头”投资建了一幢房子。为吸引客人的投其所好,取了一个有浪漫爱意的名字:“鸳鸯地”。“鸳鸯地”的服务功能,相当于当今大都市的会所,提供吃、住、娱乐一条龙服务,其服务对象多般是外地游客和商人。生意非常兴隆,一度成为老罗坊最热闹的地方。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罗坊民间把“鸳鸯地”与“青楼”同等,视“鸳鸯地”为女子卖身接客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从“鸳鸯地”遗址考察来看,建筑面积类似“司马第”和“进士第”差不多大,其建造风格也属一幢三进平房,两边也建有两排边房,边房面积不小,足可安置一个三口家庭的生活起居。有一点不同的是“鸳鸯地”建造时门口的“广场”比“进士第”、“司马第”要宽阔,而且都是麻石板铺就。这样的设置是不是为了方便“踦马下轿”的来客?

“鸳鸯地”古建前临河幸存的一处老铺面,已满目疮痍,破烂不堪 
“鸳鸯地”边房的走廊,下雨天行走不湿鞋,雨水顺暗沟流入潦河…
笔者推测,“鸳鸯地”的主体部分当时主要是用于娱乐(推牌九,打麻将,棋牌之类。)和客人用膳,而两边的边房却是用来客人住宿。当然,不排除有商人和游客携“相好”的女子同宿的情况存在。但像“青楼”那样烛影摇红,夜夜笙歌的景象,在明清时代的罗坊镇还未必有如此风花雪月的“资源”,也未必能有多少达官贵人寻花问柳在此形成“气候”。所以,笔者认为,当年罗坊的“鸳鸯地”仅是一处提供吃、住、娱乐的地方,而不是人们想像中风尘女子卖身的“青楼”。我想,也许是“鸳鸯”二字的浪漫让人们有了联想而误解了“鸳鸯地”存在的历史价值。
古建“鸳鸯地”建于何时?又毁于何时?已无从得知,查阅老“罗坊基址图”也没有“鸳鸯地”古建的标注。我家的老房子就在离“鸳鸯地”几十米远,有记忆的是“鸳鸯地”遗址是一块偌大的菜地。读小学时,我和玩伴金昌龙、陈远生、叶正兵曾在废弃的土堆里“挖宝”,也挖到过不少像铜钱、铜锁、银洋、水烟斗、瓷器等物件,然后卖给供销社的收购部。那时候这类物件不值钱,但儿时的趣事如今想起来也挺有意思。

“鸳鸯地”旧址上建的罗坊大队小学,朗朗书声不再…
目前,“鸳鸯地”只留下一排边房,但仍保存完好。这里先后曾居住廖作仁、吴元隆、罗清香、金洪生、舒宽权、舒信标、李若宽、熊兴国、熊永根等住户。解放后在原址上建有罗坊粮站、罗坊大队和罗坊大队小学。七十年代有农户开荒挖到“鸳鸯地”后墙的基脚,挖出数千块印有“吉利”二字的青砖,传这类青砖是严氏家族砖窑专制专属。由此看来,建“鸳鸯地”的主人十有八九是严氏族人了。到八十年代后,罗坊大队小学搬迁,“鸳鸯地”的旧址便陆续被农户征用建有新宅。
老罗坊历史上以“鸳鸯”冠名的“鸳鸯地”被老罗坊人视为“风尘”、“不干净”的地方,如今不但干干净净而且非常安静。曾经门前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热闹和繁华,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去而不复还,留下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子和凄凉的景象……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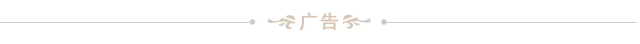
老罗坊古建故事之九:“鸳鸯第”其实是“鸳鸯地”
说起老罗坊古建“鸳鸯第”(地),恐怕只有九十岁以上的老罗坊人见过它的存在,后辈只是听说过老罗坊上街头有一处古建“鸳鸯第”(地)而已。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第”字的释义:第,表示次序:例如第一。表示科第:古代科举中称考中的叫及第,没有考中的叫落第。第,还表示贵族公卿的住宅。而所谓的门第,就是从这里衍生而来,通常指家世名望显赫。而“地”的字义非常广泛,如地方、地址、地点、地域、地貌等等。“鸳鸯地”也就是地点所指了。
尽管“鸳鸯”是爱情忠贞的像征,但如果老罗坊的一家名门望族建住宅用“鸳鸯”二字作为门第之称,不仅不符合身份的彰显,也会让人有误“风月”场所之嫌。所以,可以确定的是在罗坊历史上这里就叫“鸳鸯地”,而不是权势贵族的住宅“鸳鸯第”。民间把“鸳鸯地”叫成“鸳鸯第”是字音上的错误。


老罗坊古建“鸳鸯地”紧挨着“文林第”而建。笔者在写这篇文章前,先后走访了老罗坊几位高龄老人,又在查阅罗坊“严、罗”两大家族族谱的基础上,也对“鸳鸯地”遗址进行全面的考察。由于笔者手上可查阅的资料有限,尽管没有找到“鸳鸯地”古建有价值的信息,但也搜集到了关于“鸳鸯地”的一些传说和趣事。
老罗坊虽然开埠时间早,但进入鼎盛时期,还是从明朝商人罗英叔建镇开始。明朝建镇后的罗坊成为除奉新县城之外唯一的一个街道最完整、地域最繁荣、商贸最活跃、水陆最方便的城镇。“一河货船穿梭,三里商铺相连;日有千人游织,夜临万盏明灯”。这首民谣也许是对当时罗坊繁华似绵的真实写照。

见证了老罗坊繁华的潦河,如今已水位下降,河床见底
罗坊建镇后,因水陆两运非常通畅,来做生意的商贾和游人络绎不绝,这就给餐饮、住宿、娱乐等带来了极大的商机。民间传严氏家族中有一商人春节从外地回家乡与家人团聚,目睹罗坊新镇一派繁荣景致,头脑灵光的他当即看准了商机,便在大街繁华地段“上街头”投资建了一幢房子。为吸引客人的投其所好,取了一个有浪漫爱意的名字:“鸳鸯地”。“鸳鸯地”的服务功能,相当于当今大都市的会所,提供吃、住、娱乐一条龙服务,其服务对象多般是外地游客和商人。生意非常兴隆,一度成为老罗坊最热闹的地方。
笔者在采访中得知,罗坊民间把“鸳鸯地”与“青楼”同等,视“鸳鸯地”为女子卖身接客的地方。其实,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从“鸳鸯地”遗址考察来看,建筑面积类似“司马第”和“进士第”差不多大,其建造风格也属一幢三进平房,两边也建有两排边房,边房面积不小,足可安置一个三口家庭的生活起居。有一点不同的是“鸳鸯地”建造时门口的“广场”比“进士第”、“司马第”要宽阔,而且都是麻石板铺就。这样的设置是不是为了方便“踦马下轿”的来客?


笔者推测,“鸳鸯地”的主体部分当时主要是用于娱乐(推牌九,打麻将,棋牌之类。)和客人用膳,而两边的边房却是用来客人住宿。当然,不排除有商人和游客携“相好”的女子同宿的情况存在。但像“青楼”那样烛影摇红,夜夜笙歌的景象,在明清时代的罗坊镇还未必有如此风花雪月的“资源”,也未必能有多少达官贵人寻花问柳在此形成“气候”。所以,笔者认为,当年罗坊的“鸳鸯地”仅是一处提供吃、住、娱乐的地方,而不是人们想像中风尘女子卖身的“青楼”。我想,也许是“鸳鸯”二字的浪漫让人们有了联想而误解了“鸳鸯地”存在的历史价值。
古建“鸳鸯地”建于何时?又毁于何时?已无从得知,查阅老“罗坊基址图”也没有“鸳鸯地”古建的标注。我家的老房子就在离“鸳鸯地”几十米远,有记忆的是“鸳鸯地”遗址是一块偌大的菜地。读小学时,我和玩伴金昌龙、陈远生、叶正兵曾在废弃的土堆里“挖宝”,也挖到过不少像铜钱、铜锁、银洋、水烟斗、瓷器等物件,然后卖给供销社的收购部。那时候这类物件不值钱,但儿时的趣事如今想起来也挺有意思。

目前,“鸳鸯地”只留下一排边房,但仍保存完好。这里先后曾居住廖作仁、吴元隆、罗清香、金洪生、舒宽权、舒信标、李若宽、熊兴国、熊永根等住户。解放后在原址上建有罗坊粮站、罗坊大队和罗坊大队小学。七十年代有农户开荒挖到“鸳鸯地”后墙的基脚,挖出数千块印有“吉利”二字的青砖,传这类青砖是严氏家族砖窑专制专属。由此看来,建“鸳鸯地”的主人十有八九是严氏族人了。到八十年代后,罗坊大队小学搬迁,“鸳鸯地”的旧址便陆续被农户征用建有新宅。
老罗坊历史上以“鸳鸯”冠名的“鸳鸯地”被老罗坊人视为“风尘”、“不干净”的地方,如今不但干干净净而且非常安静。曾经门前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热闹和繁华,随着时光的流逝一去而不复还,留下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子和凄凉的景象……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甘道友
奉新罗市人,县财政局退休干部。曾聘为《中国企业家报》、《法制周报》多家报刊记者。有《那远去的日子》、《长城能推倒吗》、《活在当下》、《尽在语中》、《酒啊,酒》、《广阔天地绽芳华》专著出版。系中国新文学转型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故事协会会员,宜春作家协会会员。
-

阳光春天
冯川镇100㎡| 3室2厅 1500元 面议 -

华林广场四小周边
冯川镇110㎡| 3室2厅 0元 面议 -
迎宾公寓
冯川镇106.52㎡| 2室2厅 600元 面议 -
金鹏公馆,
冯川镇80㎡| 2室2厅 1200元 面议 -

城南新吴路小区
冯川镇171㎡| 4室2厅 800元 面议 -

洗沙路东门
冯川镇90㎡| 2室2厅 1100元 面议 -
金鹏•公馆壹号
冯川镇107㎡| 3室2厅 1000元 面议 -
冯川西路
冯川镇115㎡| 3室2厅 900元 面议 -
城南新吴路小区
冯川镇171㎡| 4室2厅 800元 面议 -

龙山紫云苑
冯川镇96㎡| 2室2厅 1000元 面议 -
朝阳小区
冯川镇86㎡| 2室2厅 600元 面议 -

城南邮政大楼大门正对面第二排(滨江花园酒店正后方)
赤岸镇135㎡| 3室2厅 700元 面议
-

中和家园
冯川镇119㎡| 3室2厅 39.8万 面议 -

星光三期
冯川镇126㎡| 3室2厅 75万 面议 -
滨江世纪城
冯川镇136㎡| 4室3厅 51万 面议 -
滨江世纪城
冯川镇131㎡| 3室2厅 51万 面议 -
恒昌花苑
冯川镇120㎡| 3室2厅 59万 面议 -

安置房一小旁边
冯川镇128㎡| 3室2厅 65万 面议 -

滨江世纪城
冯川镇136㎡| 5室3厅 50万 面议 -
中和家园
冯川镇115㎡| 3室2厅 39万 面议 -
盛世名城
冯川镇98㎡| 3室2厅 53万 面议 -
建隆华府
冯川镇126㎡| 3室2厅 57万 面议 -

江南首府•南苑
赤岸镇116㎡| 3室2厅 79.8万 面议 -
三小附近幸福家园
冯川镇116㎡| 3室2厅 69.8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上一条:通告!奉新一投诉举报渠道公布!
-
下一条:今日奉新(附3月4日奉新新闻)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