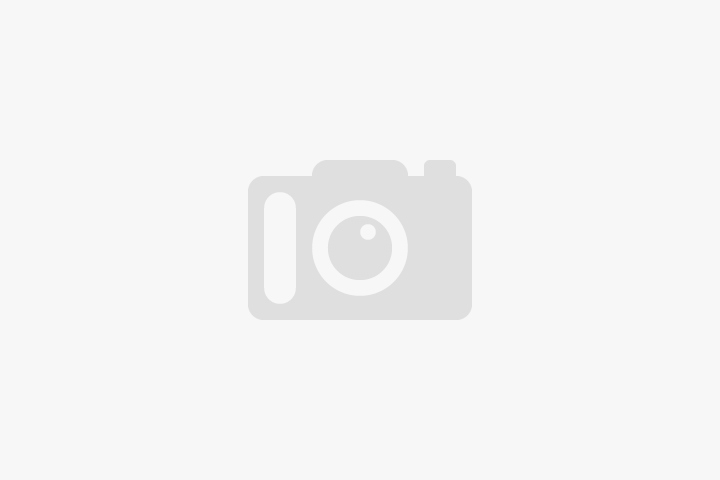微信扫一扫
永恒的记忆!四十多年前的奉新一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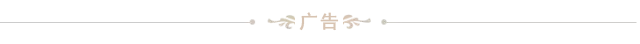
编者:从六十年校庆始,校友廖路明对母校的深情厚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仅百忙之中从京返校参加校庆,为校庆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还尽自己所能为母校作出了不少贡献。这次我找他约稿,请他写篇回忆文章,以便让现的学生们对一中历史和早年学生们是在怎样困难条件下刻苦学习的,从而对他们进行爱校教育,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成才。他说:只要是对母校和母校学生有益的事,愿尽绵薄之力,不久就为我提供这篇为六十年校庆写的文章和回忆父亲的文章。阅后,深深感受到他对父母、母校、母校老师深深的怀念、感激之情。我两篇都想转发,觉得对现在年轻一代都很有教育作用,今先发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将后续再发。通过廖路明和其他一些我有所了解的校友经历,我对“不忘来时路,方可致远行”这句话有了更深了解。

永恒的记忆
廖路明
2003年10月,是我母校﹣﹣奉新一中建校60周年。近日,负责筹办校庆的刘屏山老校长从母校打来电话,嘱我就当时在一中的学习生活方面写点东西,以作纪念。我欣然应允。主要是觉得我们那时在母校的学习生活环境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回忆一下,和后来的校友们做点交流,或许能互相有所启发。
校园印象
1978年9月,我入读奉新一中高中部。那时的一中在县城西门街。校门朝南,两扇带铁轱辘的木门对开,没挂校牌。好在出校门靠右手不远有一口水井,不熟悉的人大都是通过这口井的位置找到学校的。 
校门东侧有一个小门。大门只有在过机动车或学生集中进出校时才开。为加强管理,平时人员进出学校一般都走小门。一进小门就是传达室,有两间房子,全校的报刊、信函都在这里分发、领取,看门的老人家还兼卖一点饭菜票。 校园西侧有两排带屋檐的砖瓦结构的平房,这里是初中部的教室。当时江西仍实行二二学制,即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因此初中两个年级各占其中的一排教室,其生源主要来自城关镇及附近。高中部的教室则位于操场北面,是一栋两层楼的混凝土建筑。那时高一、高二好像各有四个班,我所在的高一(1)班的教室位于二楼最靠西侧的那一间。 
集体宿舍安排在离教室不远的一栋老式祠庙内,院中有一个长条形的天井,并排五、六间房,彼此用竹板隔断,隔音效果很差,谁要是咳嗽一声,隔壁就能听得一清二楚。好在同学中打呼噜的极少,要不然晚上休息时恐怕谁都难以安生。 宿舍用的是上下铺木制床,床板用竹片钉制而成,一般是两张床并排放置,彼此间留一点很窄的过道便于活动。一间三十平方米左右的宿舍,最少放了十张床。拥挤之状,可见一斑。 难忘的还是夜起。我们的宿舍没有卫生设施,邻近也没有厕所。虽然学校为方便学生,在宿舍的最东头放了一、二个便桶,但有的同学不知是懒还是瞌睡重,夜起时,往往不愿多走几步,干脆在宿舍门口的天井前“放肆”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只闻得一股骚味扑鼻而来。要是在夏天,加上汗味、霉味,空气更是十分的混浊。尽管住宿条件差,但都是免费的。 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简陋。记得校园的中央是一个操场,沙土地质,一劈为二就成了两个篮球场,只有正式比赛时才用石灰划线作标记,其它时间打球只能以篮球架的位置来估摸着、两个球场的球架质量也不一样。靠南场地的篮球架是木质结构,用两根木料直挺挺地支撑着,球框有点往下耷拉,球打在篮板上,要是用力大一点的话,不仅会吱呀作响,还会有点摇晃。另一个场地的球架则有点“现代化”,除篮板是木制的外,其架体则用铁管焊结而成,整体成60至70度斜角,有一点美感。 我记得当时学校只有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从未见过排球、网球和足球。说起足球,我后来还闹过一个大笑话。刚进大学的那一年9月,正值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举行,当时中国队以3:0胜了科威特,这一下整个校园都沸腾开了,大家举行游行庆祝活动,其中高呼的一句口号是“进军西班牙”。当时我茫然地问身旁一位校友,这是何意,他竟白了我一眼,意思是说,你怎么连下届世界杯决赛在哪儿举行都不知道。 我们那时既不玩足球,不懂足球,自然也就不关心足球。
五字之师
“一字之师”成语的意思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五字之师”则是我送给我的班主任罗淦先老师的“雅号”。
罗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据说文革前期曾下放在农村当农民、后来在一个乡村小学做教员。我们可能是他恢复工作后接手的第一届高中学生。他中等身材,戴一幅黑边眼镜,学者模样,写得一手好字,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吸引学生。一讲到“文革”的事,他就很激动。记得有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陶斯亮怀念她父亲陶铸的文章,他特地拿来给我们欣赏,精彩之处还会动情地给我们诵读。
罗老师对学生的管束比较严厉。我们上高中时,有的单位开始有了电视机。紧张学习之余,我们有时会偷偷躲到有电视的地方去“轻松”一下。不知罗老师从哪儿掌握了我们的动向,他时不时总去我们看电视的地方转悠。我们只要一看见他来了,就悄悄从侧门溜回教室。
其实罗老师教学还是比较注意劳逸结合的。例如在高考临战前最紧张的时刻,他利用课余时间教我们印尼民歌“梭罗河”。对我们这一群连简谱都不识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旋律简直太美妙了。至今,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罗老师,想起那挑灯夜读的紧张的学生生活。
罗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教诲,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给我以鼓励。印象最深的是高一学年结束后,我拿到罗老师给我写的评语,别的内容我已记不确切了,但有一句话我终生难忘。意思是说,该学生只要刻苦学习,用心努力,则“此木可雕也”。罗老先生可能不知道,这短短的五个字,是何等重要,在我当时因身体原因需休学一年的艰难时刻,它激励我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奋力拼搏考上大学,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为此,我在心里常常称罗老先生为“五字之师”。
上高中那几年,正常的教育体制刚刚恢复,老师们教学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有时各科任老师为课余时间给学生“开小灶”的安排还要争来争取,而且给我们补习功课从未收取过报酬。那时教我们的老师有一个普遍的特点是年纪比较大。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据说五、六十年代从新加坡还是印尼回国的老华侨,牙都掉了,看样子有60多岁(当时英语老师奇缺);教语文和数理化的老师也都在50岁左右。这些老师按过去说法有的还“出身”不好,教语文、历史的老师是“右”派,教数学的老师据说在“文革”中也被批斗过。
学生生活
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经全县统考选拔进一中的高中新生,当时年龄一般在15岁左右,大都来自农村。 由于离家较远,大多数同学在学校寄宿一日三餐也都在学校。那时粮食是计划供应物资,市场上不能随便买卖,因此,学生在学校吃饭时或者交粮票,或者从家里背来粮食。要是交粮票每斤粮得按当时国家的统一牌价交1角3分钱。另外,无论是交粮票还是交粮食,每斤都要交5分钱的柴火费。有人常戏称,说学校收的是“百家米”我们吃的是“百家饭”。 那时学校食堂也供应炒菜,一份或3分、5分、或8分、1角,不过无论便宜还是贵,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或虽来自城镇但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学生一般是不敢问津的。我们一个礼拜回一次家,返校时总是大罐小罐地从家里带菜来吃。我母亲每次为我带菜的事都要费尽心思,即要考虑下饭经吃,“站得住筷子”,又要顾及不容易变味。记得母亲经常给我做的菜有:辣椒炒咸鱼、萝卜干炒肉(或油渣)、豆腐乳、盐菜等,当然菜中的油水往往比较重。在那食油奇缺的年代,小我两岁的弟弟有时会有点嘴馋,对此还会提点小意见。母亲跟他解释,说你哥哥这一个星期天天就这两罐菜,油水重一点,经饱,不容易挨饿。 七十年代前后,在国家倡导“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大环境下,我们小学五年、初中二年就毕了业。另外,高中二年我们要完成别人三年的课程,再加上“半工半读”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是正儿八经考进一中的谓“尖子生”,但实际上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我们自己心里一清二楚。面临一年一度高考的压力,我们深感时间的紧迫,学习负担繁重。在上高中之前,外语、地理两门课从未学过,我们从高一开始学习ABC:文理科分班后,从高二开始学地理。 高中三年,我基本上坚持早上6点一过就起床,先到潦河大堤上晨练一圈,七点左右即到教室读外语或背诵语文课文,中午也是这样,午饭一吃完,很快就返回教室做作业。晚上自习每天几乎都在10点以后才收工”。记忆中,那几年早上从未睡过懒觉,中午从未有过午休,晚上很少在11点以前上过床。由于长时间的用脑、用眼过度,经常会有脑子发胀犯晕、眼睛胀痛发紧的感觉。我刚上高中时还标准1.5的视力,到高考体检时就已下降到1.0左右。 记得当时电力供应紧张,学校晚上经常出现拉闸停电的现象.停电的那一瞬间,我们都有一种轻松解脱的感受觉.但时间长了总不是办法,为此,有的同学或点起了煤油灯,或点起了蜡烛.第二天早上,教室里、学生身上都有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煤(烛)油味。 一份辛苦,一份收获。在八十年代初江西高考录取率只有4%的情况下,我们文科班有一半的同学考取了大学。现在我们中有的做了国家公务员,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已是专家教授,还有的大学毕业后回到母校当了老师,总之,都各有所成。我想大家在不断走向成功的征程中,都会想起母校对我们的培养,在心底里那份对老师的感激是永恒的。
二00三年七月十日(作者系81届校友)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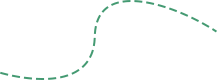

廖路明,1963年10月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1978年到奉新一中就读,1981年考入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1985年毕业。经济学博士。历任财政部办公厅新闻处长、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农业银行股权董事。
内容来源:科普信息
原题:一中专辑:校友廖路明忆母校——永恒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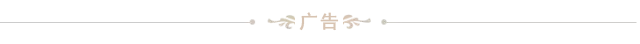
编者:从六十年校庆始,校友廖路明对母校的深情厚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仅百忙之中从京返校参加校庆,为校庆提供了很多帮助,后来还尽自己所能为母校作出了不少贡献。这次我找他约稿,请他写篇回忆文章,以便让现的学生们对一中历史和早年学生们是在怎样困难条件下刻苦学习的,从而对他们进行爱校教育,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成才。他说:只要是对母校和母校学生有益的事,愿尽绵薄之力,不久就为我提供这篇为六十年校庆写的文章和回忆父亲的文章。阅后,深深感受到他对父母、母校、母校老师深深的怀念、感激之情。我两篇都想转发,觉得对现在年轻一代都很有教育作用,今先发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将后续再发。通过廖路明和其他一些我有所了解的校友经历,我对“不忘来时路,方可致远行”这句话有了更深了解。

永恒的记忆
廖路明
校园印象


五字之师
“一字之师”成语的意思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五字之师”则是我送给我的班主任罗淦先老师的“雅号”。
罗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据说文革前期曾下放在农村当农民、后来在一个乡村小学做教员。我们可能是他恢复工作后接手的第一届高中学生。他中等身材,戴一幅黑边眼镜,学者模样,写得一手好字,课讲得生动活泼,很吸引学生。一讲到“文革”的事,他就很激动。记得有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陶斯亮怀念她父亲陶铸的文章,他特地拿来给我们欣赏,精彩之处还会动情地给我们诵读。
罗老师对学生的管束比较严厉。我们上高中时,有的单位开始有了电视机。紧张学习之余,我们有时会偷偷躲到有电视的地方去“轻松”一下。不知罗老师从哪儿掌握了我们的动向,他时不时总去我们看电视的地方转悠。我们只要一看见他来了,就悄悄从侧门溜回教室。
其实罗老师教学还是比较注意劳逸结合的。例如在高考临战前最紧张的时刻,他利用课余时间教我们印尼民歌“梭罗河”。对我们这一群连简谱都不识的农村孩子来说,那旋律简直太美妙了。至今,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罗老师,想起那挑灯夜读的紧张的学生生活。
罗老师不仅在学业上给我以教诲,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给我以鼓励。印象最深的是高一学年结束后,我拿到罗老师给我写的评语,别的内容我已记不确切了,但有一句话我终生难忘。意思是说,该学生只要刻苦学习,用心努力,则“此木可雕也”。罗老先生可能不知道,这短短的五个字,是何等重要,在我当时因身体原因需休学一年的艰难时刻,它激励我树立信心、克服困难、奋力拼搏考上大学,实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为此,我在心里常常称罗老先生为“五字之师”。
上高中那几年,正常的教育体制刚刚恢复,老师们教学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有时各科任老师为课余时间给学生“开小灶”的安排还要争来争取,而且给我们补习功课从未收取过报酬。那时教我们的老师有一个普遍的特点是年纪比较大。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据说五、六十年代从新加坡还是印尼回国的老华侨,牙都掉了,看样子有60多岁(当时英语老师奇缺);教语文和数理化的老师也都在50岁左右。这些老师按过去说法有的还“出身”不好,教语文、历史的老师是“右”派,教数学的老师据说在“文革”中也被批斗过。
学生生活
二00三年七月十日(作者系81届校友)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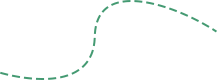

内容来源:科普信息
原题:一中专辑:校友廖路明忆母校——永恒的记忆
-
巷口村
赤岸镇140㎡| 1室1厅 500元 面议 -

巷口村
赤岸镇140㎡| 1室1厅 500元 面议 -
华林广场后
冯川镇30㎡| 1室1厅 580元 面议 -
文昌路小产权房
冯川镇140㎡| 4室2厅 800元 面议 -
滨江世纪城
冯川镇70㎡| 1室2厅 850元 面议 -
中和家园
冯川镇145㎡| 3室2厅 1200元 面议 -
天溢小区对面
冯川镇86㎡| 2室1厅 499元 面议 -
城南新吴路小区
冯川镇80㎡| 3室2厅 500元 面议 -
滨江世纪城
冯川镇135㎡| 3室2厅 880元 面议 -
金源华府
冯川镇132㎡| 3室2厅 1600元 面议 -

非小区
冯川镇108㎡| 3室2厅 600元 面议 -
城南新吴路小区
冯川镇36㎡| 1室1厅 300元 面议
-
龙山紫云苑
冯川镇155㎡| 3室2厅 59万 面议 -
金源华府
冯川镇130㎡| 3室2厅 65万 面议 -
金源华府
冯川镇130㎡| 3室2厅 78万 面议 -
融汇.幸福城
冯川镇146㎡| 3室2厅 68万 面议 -
江南首府•南苑
赤岸镇118㎡| 3室2厅 59万 面议 -
冯川西路
冯川镇98㎡| 3室2厅 37.8万 面议 -
城中心迎宾路(近华林广场)
冯川镇86㎡| 2室2厅 42万 面议 -

沿河南路路
冯川镇126㎡| 3室2厅 53万 面议 -
龙山学府
冯川镇96㎡| 3室2厅 62.8万 面议 -
冯川西络
冯川镇98㎡| 3室2厅 39万 面议 -
金鹏•公馆壹号
冯川镇93㎡| 3室2厅 63万 面议 -
冯城嘉苑
冯川镇133㎡| 3室2厅 59万 面议
自定义html广告位
-
下一条:奉新县以“小调解”促进“大治理”
 微信公众号
微信公众号